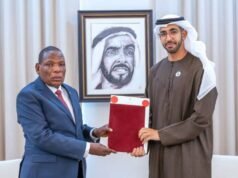dUbai在每個人的嘴唇上。社交媒體唾液的一面是關於其有組織的富裕。其他人在一個已經成為過度言論的城市中笑了。沒有英國媒體講述某人的故事,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搬到迪拜 對於較低的稅款,或者相反,迪拜夢死了»。
這座城市的狀態受益於演講所推動的這種軟力。他扮演富人和筆記。迪拜熱是民主的。這座城市是東方的埃爾多拉多(El Dorado),在資金,外籍人士和騙子的盡頭,尋找太陽。對於許多人來說,它代表了令人不安的新近視野。已經存在的未來版本。一排超級跑車俯瞰著閃閃發光的碼頭。牙齒頭,加密兄弟和嶄露頭角的企業家在牙齒頭的頭腦中的有影響力者鼓舞同一俱樂部。 Labubus Hung Designer手袋。我們愛上了這個陳詞濫調的迪拜,這是一個沒有一個地方故事的平板,合適的價格可以給您買任何東西和任何人。但是,這種二進制願景背後是看迪拜的另一種方式 – 比我們經常理解的更有趣和不尋常的地方。
過去和城市的禮物經常被簡化為迪拜市中心的2公里,遊客聚集。它是奢侈品的中心,記錄被打破了。這是一家豪華酒店和浮華餐廳的全景,擁有世界上最高建築的Burj Khalifa,提供了背景。這個形象可以是決定性的,但對迪拜的平庸歡樂和生活的痛苦幾乎沒有說明。
我記得訪問一個工業區參加詩歌 由迪拜的年輕菲律賓集體組織的閱讀。他們的工作震驚了第二代生活的怪癖。當不被公民身份奉獻時,歸屬於什麼?您如何建立換沙的基礎?這些居民是從一個強烈的層壓社會講話的,在這個社會中,身份既固定又令人驚訝。迪拜是“第三培養孩子”的自然棲息地。在任何地方,您都會聽到國際學校口音的變色龍燈籠。作為倫敦人,我與在迪拜長大的索馬里人說話,我認識到他們描述了他們的城市的瘀傷溫柔。您不能選擇家鄉。心臟是無法控制的。
今天,外籍人士已經組成 85%的迪拜人口。多虧了他們的公司,他們的學校,文化中心和社會俱樂部,各種僑民聲稱自己的存在。該市是印度以外最大的馬來亞人社區。伊朗藝術特許經營者用阿富汗雜誌擦肩。黎巴嫩房地產開發商的共享不僅僅是與北非支付訂單的低薪服務的語言。蘇丹中產階級十年在這個國家,點燃了連續的蘇丹內戰。迪拜是幾代人要求庇護和機會的移民的家園。他們的孩子麵臨恢復的挑戰。
長期以來,它也一直是一個過境中心,將旅行者與歐洲或北美航空公司未正確服務的策略聯繫起來。 (標準持票人航空公司阿聯酋航空已經利用了這一主題,生氣地 在整個1990年代和2000年中的擴張)對於許多人來說,迪拜代表了薄霧的景觀和家庭會議。純粹的必要性向城市展示了外國人。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拜訪了居住在酋長國的大家庭的成員。我們遇到的迪拜是多面有的討價還價,毛絨行李箱和含糊不清的變化之一。每年夏天,每個中途停留都揭示了一個徹底改變的城市,並為其屋頂增添了濃厚的添加。這是像純粹的ID一樣的城市,這是科學家Yasser Elshtawy所說的“城市表演”。發明術語“懷疑»,Elshtawy將城市城市景觀的超現實奢華稱為一種積極進取的現金發展模式,已成為全球計劃。迪拜領導,通常我們不願意跟隨。
後來,作為成年人,我對這座城市的旅行是由工作定義的。簡而言之,我住在一個古老的活潑社區Al Raffa。我這次發現的迪拜親吻了他的爭吵矛盾。在Deira區,我與一位尼日利亞電影製片人分享了泰米爾美食,他推薦了當地的埃塞俄比亞美髮師。在屋頂上充滿了非洲薩迪·羅迪(African Suddy Rowdy)的酒吧里,我在董事會特工遇到了一個索馬里人,他從神經崩潰中恢復過來。我們嘲笑在像迪拜一樣短暫的地方尋找穩定的荒謬性。 在另一次旅行中,埃塞俄比亞千年詳細介紹了她續簽住所簽證時遭受的屈辱。她一生都住在迪拜,無意離開。我知道另一個迪拜,即神話背後的大都市,但是這些對話仍然使我失望。該市吸引了一系列不同的新移民,那些沒想到在那裡定居的人。
迪拜一直是一個國際化的地方 – 鮑茅斯商人已經在那裡定居了幾個世紀,海上阿聯酋在印地語講話,印度的羅皮(Indian Roupie)在1960年代是當地貨幣。沒有什麼新的事實,即英國人蜂擁而至,是由英國帝國主義塑造的波斯灣。如酋長,迪拜是卡車國家之一,從19世紀初到1971年,它是波斯灣英國非正式帝國的一部分。 沒有歷史性的失憶症會改變這一點。英國外籍人士是20世紀石油繁榮的原始特徵,英國是工程師,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教育工作者。刻板印象“朱美拉·簡”(Jumeirah Jane)當時出生,一個術語指的是派遣人安靜的妻子,他們的下午在游泳池旁度過了下午。當今許多年輕的專業人士被大不列顛的破碎社會契約推遲,理想化了迪拜生活的自由骨髓。 (應該指出的是,迪拜巧克力糖果的熱情是由一位居住在城市的不列顛埃及婦女發明的。)在我自己的圈子裡,迪拜已成為工人階級畢業生的避難所,這些工人階級畢業生因多年的緊縮而感到不成比例。他們的職業生涯在海灣繁榮,護照使他們與最糟糕的剝削形式相抵觸。一次,他們佔上風。
但是西方被用來隱藏複雜性。世界其他地方是一維的,一種庸俗的比喻綜合。這種好奇心甚至延伸到了移民工人,這是海灣中脫穎而出的象徵。我們生活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家庭工人在Tiktok上講述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時代,回應了感興趣的觀眾的評論。對於那些看的人來說,從來沒有更有能力解決較低工資的移民的希望和困難。
當代海灣文學將生活呼入故事通常淪為統計數據。現在,城市工人的孩子們寫了父母的困難。克里希納達斯(Krishnadas)的迪拜·普扎(Dubai Puzha)是塔尼亞·馬利克(Tania Malik)的希望,您滿意的是,迪帕克·恩尼克里希南(Deepak unnikrishnan)暫時是人類和幽默的現代大都市。迪拜的馬拉雅拉姆語戲劇和電影代表了移民,他們爬上救助,在此過程中尋找友情。電影院繼續對移民的經歷欣賞全景,諸如Deira Diaries(2021)之類的電影在喀拉拉邦(Expatriate Keralan)的生命中回溯了四十年。這樣的故事從職業中奪走了這個人。移民工人不僅僅是可惜的對象。多刺,情人,聰明,務實;我們越來越受到他們內心的生活。
關於新加坡,杜巴斯和世界的深圳,某種類型的intect弱折磨了這些意見 西方。講故事的一半更容易消除複雜性。看玻璃和汗水,夢想和絕望的粉碎。迪拜是一件鏡子。您將看到您想看到的東西。